潘承玉: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
别一时代与文体视野中的张岱小品
潘承玉
【内容提要】
张岱向被视为晚明(性灵)小品的主要代表作家。但检核历史可以发现,张岱的几乎全部小品都成书于明亡清立后三四十年间,作为小品作家,"晚明张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但归根到底,两《梦》在鲁迅深刻指示的"比明亡略早的晚明潇洒小品"和"清初'悖谬'小品"的两类中,不属于前者而属于后者,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
【关键词】 张岱 《陶庵梦忆》 《西湖梦寻》 新小品
众所周知,晚明小品的出版和研究,在上个世纪30年代和90年代曾经出现过两次兴盛,在很多读者和学者的印象中,《陶庵梦忆》、《西湖梦寻》两书都是其间最脍炙人口的代表作品,"晚明性灵派小品大师"亦一直是人们奉送给张岱的头上桂冠。然而,并非凡存在的皆是合理的,"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石匮书自序》)(1),既是张岱考究往史的信条,也应是后人问学致知的指南。准此以观,这一"桂冠"既不符合张岱"必也寻三外野人,方晓我之衷曲"(《自为墓志铭》)之对他者的期待,也遮蔽了明清之际文学史的一个真相。
一 "清初"张岱
关于张岱的时代归属,通行的各种文学史著作,大量发表的各种论著,坊间刊行的多种明代小品文选本,几乎无一例外,都把他看作晚明人,归之晚明小品大家之列。随手翻翻,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第六十二章《公安派与竟陵派》云:"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以刘侗、徐宏祖及张岱为最著。张岱……所著《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诸作,殆为明末散文坛最高的成就。"(2)游国恩等《中国文学史》之《明中叶后的诗文》一章中《公安派和竟陵派》一节谓,"晚明产生了大量的小品散文","张岱小品散文的题材较广"(3)云云。刘大杰《中国文学发展史》之《晚明的散文与诗歌》一节亦云,"晚明新兴的散文,是公安、竟陵文学运动的产物","兼有各派之长,可称为晚明散文的代表的,是以《陶庵梦忆》、《西湖梦寻》和《琅嬛文集》著称的张岱"(4)。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之《晚明小品散文》一节,在列述公安、竟陵二派小品散文的特色后提出,"晚明散文的最后一位大家和集大成者是张岱"(5)。
但是,严格说来,张岱作为小品作家的晚明时代归属是有问题的,在晚明公安、竟陵小品的流风余韵中定位张岱并不妥当。
无庸置疑,张岱作为前代小品大家的价值和地位,是在上个世纪30年代的小品热中首先炒红,后于90年代再度得到张扬的。但有意味的是,30年代作为小品勃兴动力也是显著标志的晚明小品选本,其中影响最大的两种却并没有收张岱的作品。一是施蛰存选辑,上海光明书局1935年4月初版、1935年11月再版的《晚明二十家小品》,二是钱杏邨即阿英选辑,上海大江书店1936年7月出版的《晚明小品文库》(6)。前者收徐渭、陆树声、李维桢、屠隆、虞淳熙、汤显祖、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曹学佺、黄汝亨、张鼎、李流芳、程嘉燧、钟惺、谭元春、刘侗、陈仁锡、王思任、陈继儒等二十人的小品文三百余篇,后者收徐渭、陶望龄、江盈科、屠隆、汤宾尹、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虞淳熙、李清、李贽、刘侗、张大复、汤显祖、沈承、钟惺、谭元春、李流芳、周亮工、王猷定(误作"王遒定")等二十人的小品文六百多篇,均不见张岱之作。这到底是两位学者名流的审慎还是疏忽?---前者自序中提出的张岱小品因"易得,不再编录"明显只是一个借口,因为就当时市场的易得程度而言,袁宏道、陈继儒等人的小品并不下于张岱。
不仅如此,深入一步再追溯晚明当代最流行、影响最广的小品选本,闵景贤、何伟然按人编选,人各一卷,天启六年(时张岱三十岁,张岱文才早慧,六岁即能应对敏捷,出口成章)刊刻的《快书》五十卷,何伟然、吴从先续选,崇祯二年(张岱三十三岁)再刻的《广快书》五十卷,"割裂诸家小品",与前书共成一百家,因"与当时士习相宜"而"最传"(《四库全书提要》),内无张岱;郑元勋按体类编选,崇祯三年(张岱三十四岁)刊刻的《媚幽阁文娱初集》九卷、崇祯十二年(张岱四十三岁)再刻的《二集》十卷,"搜讨时贤杂作小品而题评之,皆芽甲一新,精彩八面"者(《初集》陈继儒序),涉及作家陈继儒、黄道周、钱谦益、倪元璐、钟惺、谭元春、董其昌、张溥、虞淳熙、黄汝亨、刘侗、李清、曹学佺、王思任、叶绍袁、黎遂球、万时华、徐世溥等六十多人,亦无张岱;何伟然、丁允和同样按人编选,人各二卷,陆云龙评,崇祯六年(张岱三十七岁)刊刻的《皇明十六名家小品》三十二卷,包括屠隆、徐渭、李维桢、董其昌、汤显祖、虞淳熙、黄汝亨、王思任、袁宏道、文翔凤、曹学佺、陈继儒、袁中道、陈仁锡、钟惺、张鼎等之作,同样没有张岱。实际上,除了以上这些,今天所能见到的其他所有晚明当代小品选本中也都找不到张岱的踪影。甚至任何晚明当代文人别集中也找不到张岱作为晚明小品作家存在的证据。
归根到底,张岱的小品不论是作为选本选收对象还是单行专集,在明亡之前根本就没有刊刻行世过(是否创作亦甚可疑),遑论他在晚明小品领域的影响和地位,更遑论他是晚明小品的代表作家了。
分析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把张岱看作晚明小品代表作家的原因,主要应是遵从惯例。吴承学先生《晚明小品研究》的处理最为典型。该书绪论开宗明义提出:"所谓晚明,传统是指明代万历年间至明朝灭亡(1573-1644)这段七十余年的历史。……比较难以区分的是明末清初的作家,有时难以明确是明人还是清人,碰上这种情况,我采取的态度是'吾从众'---依照学术界的惯例。"(7)披览该书第二至第六章重点评价的十八位晚明作家,当得"吾从众"的唯一人物就是张岱。而考察这一惯例的形成和延续,显然和上个世纪几个重要历史时期得风气之先者的论述相关。例如,上个世纪30年代小品高潮之际,由刘大杰校点、上海贝叶山房1935年铅印出版,也是民国成立以来张岱文集首次刊行的《琅嬛文集》(8),末附成都大学教授卢前跋转述该校资深学者刘鉴泉之论云:"近世新文艺,其原盖出于浙东史派,而晚明诸家为之先河,张宗子岱实启之也。"两年后,周作人在影响很大的《再谈俳文》一文中再次称引刘氏之语,以"我们可不必再辞费"(9)云云对刘氏理论高度肯定,实际上也就高度肯定了刘氏说的内在意涵---张岱为"晚明诸家"之一甚至是之首。或许和这样的学术影响相关,新中国成立以后第一部大量印行的大部头文学史著作、1957年由作家出版社推出的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方如上所引将张岱明确归入晚明"天启、崇祯间的散文作家"行列。郑著的精彩才情和它的广泛发行(10),无形中使"晚明张岱"的理念更加深入人心。这一理念的根深蒂固,可从袁行霈等《中国文学史》中这段误引文字见出:"明人祁彪佳说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西湖梦寻序》)"(11)众所周知,祁彪佳愤明之亡,自沉于水,在南明弘光朝覆灭不久的顺治二年闰六月;如果这段引述文字无误,它意味着,顺治二年四十九岁之前,张岱的《西湖梦寻》就已写成,张岱晚明小品作家的时代属性确然无疑。然而,各种版本的祁彪佳撰著中既无此《西湖梦寻序》,张岱的自序更确凿表明《西湖梦寻》成书的时间乃在康熙十年其七十五岁左右。查康熙五十七年凤嬉堂始刻本《西湖梦寻》可知,此序原来是祁彪佳族兄祁豸佳所为。据《嘉庆山阴县志》,此人明亡后家居数十载始以寿终。将祁豸佳错看成祁彪佳,深层的心理原因离不开"晚明张岱"的理念作用;而这一误会的形成,反过来又适以坐实和强化"晚明张岱"的理念。当然,并非没有人注意到这个事实。如周作人在论述晚明以后的文学运动时就曾写到,"后来公安、竟陵两派文学融合起来,产生了清初张岱诸人的作品"(12),明确提出了"清初张岱"的时代定位。当代也有少数文学史家注意到,"张岱的许多小品文实际是作于清初"(13)。但是,在他们的逻辑理路中,无疑是把清初小品看作晚明小品的等质延续,把清初张岱与晚明张岱等量齐观,从而最终用后者的概念涵容前者了。
由此可见,作为小品作家,"晚明张岱"实际上是不存在的,存在的只有"清初张岱";并非仅仅是张岱的许多小品,而是张岱的几乎全部小品,实际上都是在清初创作的。向被看作张岱影响最大的两部小品文集:《陶庵梦忆》,据自序"陶庵国破家亡"、"繁华靡丽,过眼皆空,五十年来,总成一梦"、"遥思往事,忆即书之"等内容,始撰于绍兴鲁监国政权抗清失败、浙东二次沦陷、张岱时年五十岁的顺治三年;据原抄本和《砚云甲编》本的佚名序"今已矣,三十年来,杜门谢客"、"为序而藏之"等内容,当定稿于浙东二次沦陷后三十年的康熙十五年。《西湖梦寻》,据康熙五十七年初刻本自序"前甲午、丁酉,两至西湖"、"余乃急急走避,谓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等内容和末尾"岁辛亥七月"的署年,以及李长祥序"甲申三月,一梦蹊跷,三十年来,若魇若呓,未得即醒"云云,初稿当酝酿于顺治十七年稍后,而成书于康熙十年,但到康熙十三年可能仍在修改之中。也属小品文集的《琅嬛文集》,据王雨谦序"甲申以后,屏弃浮云,益肆力于文章,自其策论、辞赋、传记、笺赞之类,旁及题额、柱铭,出其大力,为能登之重渊,而明诸日月,题曰《琅嬛文集》",亦全为明亡以后之作,其中各家广泛瞩目的《石匮书自序》、《自为墓志铭》即分别作于康熙三年和康熙四年;卷五《蝶庵题像》"八十一年,穷愁卓荦"等表明,撰就最迟者当不早于康熙十六年其八十一岁时。
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张岱与其说是"晚明"小品的殿军,毋宁说是"清初"小品的白眉,他的创作不是晚明公安、竟陵的余绪,而代表了小品在明清易代后的崭新动向。
二 "史文"两《梦》
近今人津津乐道于张岱的小品创作成就,晚明当代人亦沾沾自炫于小品"丽典新声"、"盛于昭代"(郑元勋编《媚幽阁文娱初集》卷首陈继儒、唐显臣序引郑元勋语)。然而,不为时人所动,亦无意于为后人预作铺垫的是,拥有很多小品名家知己的张岱,却并没有什么浓厚的"小品"情结。如其《祭周戬伯文》提到自己的生平所好与所遇之幸云:
余好举业,则有黄贞父、陆景邺二先生、马巽青(倩)、赵驯虎为时艺知己;余好古作,则有王谑庵年祖、倪鸿宝、陈木叔为古文知己;余好游览,则有刘同人、祁世培为山水知己;余好诗词,则有王予庵、王白岳、张毅儒为诗学知己;余好书画,则有陈章侯、姚简叔为字画知己;余好填词,则有袁箨庵、祁止祥为曲学知己;余好作史,则有黄石斋、李研斋为史学知己;余好参禅,则有祁文载、具和尚为禅学知己。
除了举业时文系其早年谋求仕进之道,游览、参禅、填词、书画为其前半生纨绔习气和名士风流所在外,古文、诗词与史学,乃其毕生文学与学术追求,这里并没有一字提到小品;所言黄汝亨、王思任、倪元璐、刘侗、黄道周、李长祥等虽都是晚明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但他们却都是以其他身份被其看作人生知己,这进一步反映出张岱对小品的漠然态度。
会不会他的"古文"概念就是与八股时文相对的一般散体文学,已经包含今人所说的"与传统古文和时文相对"(14)、"替代传统散文(古文)在晚明时期独领风骚"(15)的小品在内?从他自认的古文三知己的情况和张岱对他们的具体评价来看,这种可能性不大;从他对整个中晚明散文发展的评价来看,更可以完全否定。就前者而言,王思任虽以小品知名,亦极看重传统古文,如将天台最胜处喻为"绕肠雄气,满腹古文,郁郁苍苍" (《王季重十种·游唤》) ,自述游记创作以柳宗元为鉴戒而兼取"苏长公之疏畅,王履道之幽深,元美之萧雅,李于鳞之生险,袁中郎之峭隽"(《南明纪游序》,《王季重十种·杂序》),借鉴古今古文名家远多于当代小品领袖;在今人所指的小品散文和古文体制的游记散文和议论散文等三类创作中,古文的成就更高,其中游记散文尤其"取得较高成就",代表了王思任散文的主要特色(16)。倪元璐的题跋、短札固然时见小品灵气,但他对传统古文载道宗旨和创作取向的重视,更体现出古文载道派的本色,如云"柳子曰感恩报国,惟有文章","道之可以起智造力,无如是器良者"(《题张肯仲艺》,《倪文贞集》卷十六),"今之为文者不秉法古人而自不见性" (《吴澹人庶常别言序》,同书卷七) ;创作上获得的历史定评"文章典雅,为馆阁所宗" (《四库全书提要·倪文贞集》) 亦纯粹是就其古文体制的制诰文字而言。陈函辉,"海内称文章风流豪荡者,推天台陈君焉"(邵廷采《东南纪事》卷五《陈函辉》),其所擅的文章更与小品毫不相关,据存世文集和殉节前自著《寒山年谱》,十一岁"究心古学",十二岁"作《仁物论》数千言",十三岁"先太夫人口授《左传》、《汉书》,遂肆志学古",四十岁"文满天下,多谈经济,不复言帖括铅椠业"(《孤忠遗稿》卷一),一生所好即格物论理、弘道济世的古文。张岱《王谑庵先生传》承认王思任"《及幼》小题,直与钱鹤滩、汤海若争坐位",但更盛赞其游记散文"笔悍而胆怒,眼俊而舌尖,恣意描摹,尽情刻画,文誉鹊起";其《石匮书后集》之《倪元璐列传》对倪元璐小品不着一字,而大力渲染其古文体制的奏疏"天下传诵,纸贵洛阳",至称"上为拈之屏间";同书《陈函辉列传》用大半篇幅一字不漏地收录其传诵一时的古文代表作《起义勤王檄》。凡此可见张岱对古文的垂青,而小品则难分其幸。就后者而言,《石匮书·文苑列传·总论》在批评明代八股害文,文风长期萎靡之后,云:"孝庙(按即弘治)以后,文士蔚起,代不乏人,古奥如李空同,葩藻如何大复,华赡如李西涯,博洽如唐荆川,雄浑如李沧溟,苍茫如王弇州;后自七子之纵横,当世徐文长、袁中郎思以奇颖救之,而失于草率;刘子威、汤若士思以警练救之,而失于浓冶;钟伯敬、谭友夏思以澹远救之,而失于浅薄。"将晚明话语环境一直诟病不休的七子派和非七子派等明中后期诸大家古文,一体放在明代散文演变的历史过程中考察,突出其振衰起敝之功,并对各家风格不吝张皇赞誉之辞,而对晚明士人极为艳称的诸大家小品,则直指其"草率"、"浅薄"之失,如此字眼迹近对其创作态度和创作水准的整个否定,也极类后来四库馆臣对晚明小品的鄙薄用辞,两相对照,尽见张岱对古文与小品的抑扬取舍。
由此可见,张岱的倾向确实在古文,他对小品并无好感;他在后人心目中虽然有"小品圣手"之称,但那些被视为最经典小品的文字包括两《梦》,却并不是他小品爱好的产物。直言之,我们由此可见,张岱的倾向确实在古文,他对小品并无好感;他在后人心目中虽然有"小品圣手"之称,但那些被视为最经典小品的文字包括两《梦》,却并不是他小品爱好的产物。直言之,我们不妨把它们就视为古文。
古文是讲究载"道"的,道的实现途径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个途径就是撰作历史。一者,正如"史之为务,必藉于文"(《史通·内篇·叙事》),"言文章者宗《左》、《史》"(《文史通义》卷四),"文必秦汉"的大端也就是取法《左传》、《史记》等史书,文与史、古文爱好与史学追求向来就是一体两面、交互为用的。二者,所谓"经世之务,莫备于史"(魏禧《魏叔子文集》卷八《左传经世序》),"六经皆史"(李贽《焚书》卷五《经史相为表里》,非仅章学诚《文史通义》),在史官本位的传统文化中,撰述历史本就是文人的名山事业。三者,如其自云"自幸吾先太史有志,思附谈、迁,遂使余小子何知,欲追彪、固"(《征修明史檄》),张岱出身在一个了不起的史学世家。高祖天复专攻史部地理类,著有大部头的《皇舆考》以"规《明一统志》之失"(《四库全书提要》),并创修《山阴县志》;曾祖元忭著有探讨历史编纂学理论的《读史肤评》,并推扬乃父之志,续完《山阴县志》,又自撰《绍兴府志》、《会稽县志》、《云门志略》等,在史部地理类乡邦著作的撰写中取得骄人的"创格"成就(《四库全书提要·绍兴府志》 ;亲承教泽的祖父汝霖曾主盟南京"读史社",倾动一时,等。而从其在明亡之前五十年间刊刻行世的唯一著作就是史部传记体的《古今义烈传》这一事实,和明亡后"千秋万岁后,岂遂无荣辱?但恨《石匮书》,此身修不足"(《和挽歌辞》)、"陶庵国破家亡,无所归止……每欲引决,因《石匮书》未成,尚视息人世"(《陶庵梦忆序》) 等自道来看,"余好作史"的史学追求确乎在其一生的全部文化活动中占据了核心的位置。其所以如此,除了上述诸因素,张岱本人的主体人格意志显然发挥了决定作用。《自为墓志铭》自道"称之以智慧人可,称之以愚蠢人亦可;称之以强项人可,称之以柔弱人亦可",在自视点和外视点的交汇、自认和自谦的统一中昭示人们,"智慧人"和"强项人"乃是其主体人格的根本特点。如果说,明亡之前,主要作为智慧人,张岱天才地警觉,"世之士人,空列须眉,终鲜仁义 "(《古今义烈传·凡例》;张岱始事该书编撰时仅二十二岁),士风靡烂至极;敏锐地发现,"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匮书自序》,所以,他才要穿穴史乘,提携义烈,以振士气,才要广搜博采,秦铜相照,必成信史,才有了一部史书的刊刻行世和另一部史书的草创。那么,明亡之后,则主要作为强项人,张岱景仰古今抗暴复国志士的悲壮事迹(如《乐府》组诗所述)和宋末文天祥、郑思肖等反元民族英雄和遗民的千古节义(见《石匮书后集》之《刘宗周列传》、《祁彪佳列传》等传末"石匮书曰"),继承了华夷之辨的强烈民族思想,形成不臣异族暴政的坚定民族气节。如其反讥《论语·夷狄章》云:"余遭乱世,见夷狄之有君,较之中华更甚,如女直之芟夷宗党,诛戮功臣,十停去九,而寂不敢动。如吾明建文之稍虐宗藩,而靖难兵起,有愧于夷狄多矣。"(《四书遇·论语》 其内残犹且如此,其铁蹄南下到处屠城血洗之凶暴夫复何言!他描绘清人统治下的祖国,"中原何处是?到面尽腥风。石马嘶荒冢,铜驼泣故宫。星辰沧海北,风雨大江东"(《听太常弹琴和诗》之一),完全是一派腥风荒冢,黑暗如磐,飘摇陆沉的恐怖绝望景象。所以,他更加意识到为故国保留信史的紧迫,同时也萌生借助撰述来抒发其民族悲愤,寄托其故国哀思,成就其不臣异族之心史的强烈冲动。如云,"皇明无史乘,五凤属谁修?九九藏《心史》,三三秘禹畴"(《谢周戬伯校雠〈石匮书〉二首》),"余与三外老,抱痛同在腹"(《读郑所南〈心史〉》)。《心史》乃宋遗民郑思肖(字所南、忆翁,号三外野人)抒写亡国悲愤,长期沉井之作,《久久书》乃其中"九九错综书之,又取久久之义"名之 (《心史·久久书·自序》) 的抗元起义盟檄及跋文集,"三三禹畴"即《尚书·洪范》中禹所掌握的"洪范九畴",与《春秋公羊传》讲的都是经世大法。有了这种为故国修史、舍我其谁的自信、自励,这种视宣扬不臣异族的民族气节、眷念故国的民族情怀为最神圣使命的自责、自强,才有了《石匮书》的五易其稿,九正其讹,才有了《石匮书》之外的其他撰述活动。这样的民族气节,应该就是张岱古文的"道";对两《梦》的观照,也不应脱离其一生文化活动中最核心、最重要的这一史学追求的背景。张岱明亡后所作《史阙·南宋纪》中有关于南宋《清明上河图》的一段议论:
张择端《清明上河图》,因南渡后想见汴京旧事,故摩写不遗余力。……嗟乎!南渡后人但知临安富丽,又谁念故都风物?择端此图,即谓忠简请回鸾表可也。
"忠简"即两宋之交抗金民族英雄宗泽,他于汴京陷落、高宗南徙之后,"前后请上还京二十余奏",卒时"但呼过河者三而薨","遗表犹赞上还京"(《宋史》卷三百六十本传)。黄裳提出,"这短短的一节话,可以看做《梦忆》、《梦寻》的跋语";还说,包括小品在内的张岱撰述,"大多是与史部有牵连的,可以看作一种突出的特色"(17)。笔者以为,这是对两《梦》乃至张岱全部撰述底蕴的一种精当体察,是非常贴近张岱之作要旨的。如果说,在张岱眼中,《清明上河图》就是张择端不遗余力摩写北宋故都风物,以为历史见证,也作为自己怀念故国之情的慰藉,并希望使人感激而起的图画之史,那么,作为后人的我们,更有理由把两《梦》看作张岱有关大明故国风物、山川的有同样目的和功用的文字之史。《梦忆》自序:"偶拈一则,如游旧径,如见故人,翻用自喜。"《梦寻》自序:"余为西湖而来,今所见若此,反不若保我梦中之西湖,尚得完全无恙。……余犹山中人,归自海上,盛称海错之美,乡人竞来共舐其眼。"历史见证、感情慰藉、期有兴感,何所缺焉?张岱在文字中反复提到郑思肖,《石匮书》之得名、寓意既从其《铁函心史》而来,两《梦》之得名、寓意实亦如是。《心史》卷上《中兴集·忆梦哭歌》小序:"五月二十一日夜,梦游西湖上,旧游宛然。行至戎马蹂践之地,忆今天子不在咸阳宫,大哭陨绝而觉,遂作此歌。"《梦寻》题材的选择和得名由此直接而来,《梦忆》的得名亦与此以及郑思肖的字"忆翁"直接相关,由此可见,两《梦》确实是张岱对大明故国山川、大明故国风物的恸哭之心史!
从《梦寻》作为张岱被《四库全书》著录(存目)的唯一著作,所处的位置在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从与两《梦》在题材和体例上有密切关系的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吴自牧《梦粱录》、周密《武林旧事》、田汝成《西湖游览志》、刘侗《帝京景物略》等书,在各种目录学文献中也都处于史部地理类山川之属或者杂记之属等情况,我们可以进一步确认,两《梦》在史体上属于史部地理类。如前所述,这正是张门史学所最擅长的史学门类。
综上所述,两《梦》不是张岱自觉的小品追求的产物,而是其载道济世的古文爱好和信史更兼心史的遗民史学追求的结晶,是从异族统治的黑暗中淬砺而出的特殊"史文";坚定的民族气节、深沉的故国情怀,就是这史文所载的"道"。那种把张岱小品仅仅看作其自道的"忏悔"之什,或当作"繁华颂歌"(18)的观点,显然失之肤泛。
三 结论:新小品的"白眉"
称两《梦》是"史文",并非真的要全盘否定它们的小品属性,小品毕竟是包容很广的文类概念而不是单一的文体名称,古人目录文献中载录为史文而今人视为小品者多矣。关键的问题是,我们无法否认早年的张岱对晚明小品诸浪尖人物曾经下过很深的研究工夫,如云,后虽自悔,"少喜文长,遂学文长诗,因中郎喜文长诗而并学","后喜钟、谭诗","非钟、谭则一字不敢置笔,刻苦十年"(《琅??诗集自序》),诗文一体,对徐、袁、钟、谭诸人诗的长久浸润必然带来对他们小品散文的相当熏染;也无法否认在明亡前近半个世纪的岁月里他密切接触,视为忘年老友或人生知己的陈继儒(1558-1639)、黄汝亨(1558-1626)、王思任(1575-1646)、刘侗(约1593-1637)、倪元璐(1593-1644)、黄道周(1585-1646)等,都是晚明当世赫赫有名的小品大家;更无法否认两《梦》娓谈絮语、如怨如慕,"奇情奇文,引人入胜,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砚云甲编本金忠淳《陶庵梦忆跋》,"有刘同人之生辣,有袁中郎之倩丽,有王季重之诙谐,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典型地体现出小品的语体风格和情采魅力,明显地涵容了晚明小品的审美精华(其被今人视为晚明小品集大成者的主要原因或即在此)。但是,如前所述,两《梦》均成书于明亡三十年前后,这与晚明小品的长盛时代万历中到崇祯初,已有约四十年的时间距离。这四十年既是中国历史发生重大转折,最终"夷狄滑夏"、尘埃落定的时间,也是晚明小品逐渐发生裂变,从而产生一种新小品的时间。
上个世纪30年代现代文学界发生的小品宗尚之争,已然划出这两种小品的界线所在。争论的一方,"性灵小品"的提倡者林语堂主张,小品"特以自我为中心"(19),"取较闲适之笔调,语出性灵",声称"无论题目是多么严重,多么重要,牵涉到祖国的惨变和动乱,或文明在疯狂的政治思想的洪流中的毁灭……这种观念依然是可以用一种不经意的、悠闲的、亲切的态度表现出来"。在根本上,他用一个"闲"字抹掉其理路中包含的表现自我,张扬性灵,继续"五四"新文化追求个性解放精神的积极意义,而把小品定位为"有闲生活"者"善用其闲"的一种"乐趣"(20)。他为此类小品找到的中国祖宗,就是公安派袁宏道等人的晚明小品。争论的另一方,堪称现代"激进小品"的主要实践者鲁迅,则明确反对小品"只是以'闲适'为主",反对使小品沦落为仅仅是"枕边厕上,车里舟中"的"极好的消遣品"(21),对"从血泊里寻出闲适来"的小品式"聪明"更是深表齿冷(22)。1933年8月,他提出著名的"匕首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并不是'小摆设'。"和林语堂一样,鲁迅的心里也有前代的榜样。他这样写道:"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种作风,也触着了满洲君臣的心病……"(23)显然,鲁迅的榜样就在这"明末的小品"之中。1934年12月,他提出"比明亡略早的晚明名家的潇洒小品在现在的盛行"(24)的命题,这是对林语堂、周作人所提"晚明小品"实质的精确判断,也是对自己所提"明末小品"概念内涵前一半即"颓放"和"吟风弄月"成分的进一步澄清和排除。1935年12月,鲁迅明确道出了心目中的真正榜样: ……当然也有人预感到危难,后来是身历了危难的,所以小品文中,有时也夹着感愤,但在文字狱时,都被销毁了,劈板了,于是我们所见,就只剩下了"天马行空"似的超然的性灵。
这经过清朝检选的"性灵",到得现在,却刚刚相宜,有明末的洒脱,无清初的所谓"悖谬"……(25)
被满清文字狱切分取舍所掩盖的面貌,经过鲁迅的再一次切分取舍恢复历史的本来面目:"比明亡略早的晚明潇洒小品"和"清初'悖谬'小品",这就是文学史上曾经存在的两种小品形态。这两种小品的根本不同,前者归根到底是一种娱乐艺术,纯粹诉诸一己生活狭隘性灵的艺术,很大程度上也是为小品而小品的艺术,而后者则是一种不平之鸣,是从个人角度去关怀和体验国家民族兴亡的心灵的写照,是无意为小品而小品,而以古文为小品的文化追求。业师《晚明小品研究》第十一章中所考察的徐芳、傅占衡、叶绍袁、陈弘绪、黄淳耀、夏完淳等南明殉国忠节和遗民的作品,《四照堂文集》中顺治年间王猷定的作品,《河滨遗集》、《牧斋有学集》中顺治年间李楷、钱谦益的作品,《遍行堂集》中康熙年间金堡的作品,以及鲁迅在《花边文学·读书忌》中特别感慨的屈大均康熙年间的作品,等等,都属这后一类小品,这是以殉南明忠节和遗民小品为主而又涉及范围非常广泛的一类作品。
以两《梦》为代表的张岱小品,虽然锋芒比较收敛,血泪含而未溢(《梦寻》之在文字狱中漏网与此相关),但作为连周作人也曾承认的"反抗的"(26)作品,应该也是这种新小品的代表。考虑到其情感流露的深沉含蓄、表现境界的冰雪滢澈、文化蕴涵的寻味不尽、语言文字的写照传神等优长,加以比较集中的规模,称其为这种新小品的白眉,应该是比较允当的。它和多数超然的"小摆设"般的晚明小品,属于两个时代,不可相提并论。 论文代写
以为张岱小品大多只是自己"闲情逸志"的"酣畅淋漓",只是晚明公安三袁"独抒性灵"作风的铺张扬厉(27),或者以为只是晚明众多"山水小品"中的"生色"者,不属于"清初的遗民小品"范围(28),这样的看法,恐怕太埋没张岱的深心,有负其"晓我衷曲"的期待。
[作者简介]潘承玉,1966年生,2002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中文系,获博士学位,现为绍兴文理学院中文系副教授。发表过专著《清初诗坛:卓尔堪与〈遗民诗〉研究》等。
注释:
1本文所引张岱文字除另有说明者外,均据夏咸淳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张岱诗文集》,为避烦琐,只随文标出篇名,不出注。其他古籍引文亦仅随文标出书名、篇名。
2《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下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1版,第968页。
3《中国文学史》第四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72页。
4《中国文学发展史》下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933、938页。
5《中国文学史》下册,复旦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305页。
6 1989年河北人民出版社再版,改题亦为《晚明二十家小品》。
7《晚明小品研究》,江苏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5页。
8作为"中国文学珍本丛书"第一辑第十种,贝叶山房本刊行于1935年11月;同时上海国学研究社"国学珍本丛书"本刊行后此一月,无卢前跋。
9钟叔河编《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湖南文艺出版社1998年版,第427页。
10据北京出版社1999年新1版"重印后记",仅自1957年作家出版社第1版第1次印刷至1982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第5次印刷,印数就达89000册,1982年以后各家出版社竞相出版更甚。
11《中国文学史》第四册,第212页。
12《周作人自编文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版,第26页。
13章培恒、骆玉明《中国文学史》下册,第393页。
14欧明俊《论晚明人的"小品"观》,载《文学遗产》1999年第5期。
15李金松《晚明小品新论》,载《社会科学战线》1995年第6期。
16徐志啸《论王思任的散文》,载《文学遗产》1993年第4期。
17《黄裳书话》,北京出版社1997年版,第149、144页。
18王海燕《〈陶庵梦忆〉主旨新说》,载《山东大学学报》1998年第3期。
19《林语堂全集》第十七卷,作家出版社1996年版,第180页。
20《林语堂全集》第十八卷,第1-10、23页。
作文 /
21《鲁迅全集》第五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484、603页。
22 《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69页。
23《鲁迅全集》第四卷,第570-571页。
24《鲁迅全集》第六卷,第167页。
25《鲁迅全集》第六卷,第423页。
26《周作人文类编》第三卷,第645页。
27胡冠莹《从李贽、三袁到张岱》,载孙以昭、陶新民主编《中国古代散文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25页。
28陈书良、邓宪春《中国小品文史》,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第219、238-245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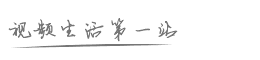






 quyi56
quyi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