尹恭弘:张岱的小品艺术
张岱的小品艺术
——自觉的忏悔意识
尹恭弘
明清之际的著名小品作家张岱,具有较为自觉的忏悔意识,他总是以“梦寻”、“梦忆”的形式,反映晚明时期的风俗习惯、世态人情,表现时代的沧桑,表现他自己感情和心态的变迁。由于他描绘的生活形态较为逼真,他倾吐的情怀较为真挚,所以他创作的小品长期以来深受读者的欢迎。
(忏悔、真情、清新、沧桑这些特点都是红楼梦的特色。)
张岱(1597-1690),字宗子,又字石公,号陶庵,又号蝶庵居士,山阴(今浙江绍兴)人。他出身于一个数世通显的仕宦家庭。高祖张天复,是嘉靖间进士。曾祖张元汴,是隆庆五年的状元。祖父张汝霖,是万历年间的进士。而且,从他祖父起,他家生活更加奢侈,讲究声伎,家庭的艺术氛围甚浓。此外,他家藏书很多,他的高祖、曾祖、祖父三代积书多达三万余卷,他祖父还允许张岱充分利用这些书籍,说:“诸孙中惟尔好书,尔要看者,随意携去。”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张岱的影响是多方面的,既使张岱生活优裕、交游广泛,又培养了他较高的文化修养和艺术修养,勤于著述。明亡后,避居深山,仍完成多种著述。因此,他著作甚丰,有《琅嬛文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く石匱书〉、《四书遇〉、《张氏家谱》、《义烈传》、《明易〉、《大易用)、《史阙》、《说铃昌谷解》、《快园道古〉、《亻奚囊十集)、く一卷冰雪文》、く于越有明代三不朽图赞〉、《夜航船〉く张子文秕〉、く张子诗秕〉、《琅嬛山 馆笔记》等,其中不少著述已散佚。
张岱的两部著名的小品集《陶庵梦忆〉、く西湖梦寻〉之所以能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文化动因。他在明亡之后,就能以较为自觉的忏悔意识回忆往事、生发感慨,首先与他在明亡之前就能坚持修史、有独立思考问题的习惯有一定的联系。
张岱酷爱读书,除家藏数万卷书籍外,几十年来,他自己也聚书不下三万卷。他对历史、尤其是明代史事特感兴趣,因而逐渐萌发了自己修明史的愿望和决心。他对明代一些史书提出过严肃的批评:“宋景濂撰く洪武实录〉:事皆改窜,罪在重修;姚广孝著《永乐全书》,语欲隐微,很多曲笔。后焦芳以金王秉轴,邱濬以奷奸险操觚。正德编年,杨廷和以掩非佈过;明伦大曲,张孚敬以矫枉持偏。后至党附多人,以清流而共操月旦;因使力翻三案,以阍竖而自擅纂修。黑白既淆,虎观石渠尚难取信;玄黄方起,麟经夏五不肯阙疑。博治如王弁州,但夸门第;古炼如郑瑞简,纯用墓铭。く续疲书〉原非真本,《献征录》未是全书。《名山藏〉有拔十得五之誉,く大政记〉有挂一漏万之讥。”(《征修明史檄》)因而,他认为:“第见有明一代,国史失诬,家史失谀,野史失臆,故以二百八十二年总成一诬妄之世界。”(石匮书序》)张岱对具体史书的得失评价的正确与否,暂且勿论,但他要求修史“事必求真,语务必确”的标准,是值得称赞的。从崇祯元年(1628)起,他正式开始写作明代历史,一直到明亡,这部史书尚未完成。这部史书,他命名为《石匮书》。く石匮书》的史学价值,史学界自有公断。但从文学角度看,张岱通过修史,自然具有洞悉古今变化的历史眼光,一旦国破家亡,这种历史眼光必然上升为较为自觉的忏悔意识,这对他的小品创作产生了积极影响。张岱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他在研读《四书》时,就有这方面的宝贵经验,并且在明亡前编写了《四书遇》这部书。他在 自序里写道:“余幼遵大父教,不读朱注,凡看经书,未尝敢以各家注疏横据胸中。正襟危坐,朗通白文数十余过,其意义忽忽有省。间有不能强解者,无意无义,贮之胸中,或一年,或二年,或读他书,或听人议论,或见山川云物,鸟兽虫鱼,触目惊心,忽于此书有悟,取而出之,名日《四书遇》。盖遇之云者,谓不于其家,不于其寓,直于途次之中邂逅遇之也。”看来,这部书不少议论,是他独到的领悟和理解。张岱对这部书自视甚高,“余遭乱离两载,东弃西走,身无长物,委弃无余,独于此书,收之箧底,不遗只字。”当然,从哲学思想角度看,这部书并无什么精辟见解。但是,他那独立思考的精神,无疑对他创作上形成独待的创作个性起着积极作用。
显而易见,在明亡之前,张岱那些丰富多彩的生活,洞察古今变化的历史眼光,独立思考的精神,为他创作具有独特风格的小品打下了良好的基础。但是,最后促使他完成《陶庵梦忆西湖梦寻〉等小品创作的是动荡的时代和社会,他在《自为墓志铭)中写道:“年至五十,国破家亡,避迹山居,所存者破床碎几,折鼎病琴,与残书数帙,缺砚一方而已。布衣蔬食,常至断炊。”甲申以后,悠悠忽忽,既不能觅死,又不能聊生,白发婆娑,犹视息人世。"这时他生活困顿、心绪苍凉,但也促使他猛醒。这是他较为自觉地形成忏悔意识的时代背景。
他始终坚持修史,对尚未完成的《石匱书》,他“携其副本,屏迹深山,又研究十年而甫能成帙。”一个具有历史感的作家,必然会对自己的身世产生一种负罪感。当年他精吃螃蟹,现在想来就不能不产生惭愧之情:“一到十月,余与友人兄弟辈立蟹会,期于午后至,煮蟹食之,人六只,恐冷腥,迭番煮之。从以肥腊鸭牛乳酪,醉蚶如琥珀,以鸭汁煮白菜如玉版,果蒎以谢橘、以风栗、以风菱,饮以玉壶冰,蔬以具坑笋,饭以新余杭白,濑以兰雪 茶。徭今思之,真如天厨仙供,酒醉饭饱,惭愧惭愧。”明亡后他两次重返西湖,看到的情景又使他生发无限的感慨:“如涌金门商氏之楼外楼、祁氏之偶居、铁氏余氏之别墅及余家之寄园带湖庄,仅存瓦砾,则是余梦中所有者,反为西湖所无。及至断桥一望,凡昔日之弱柳天桃、歌楼舞榭,如洪水湮没,百不存矣。”一个具有深沉忏悔意识的人,往往容易产生逆反心理,越是失去的东西,对它的回忆越是津津有味、如醉如痴。这正是张岱创作《陶庵梦忆)、く西湖梦寻)等小品的感情基础和心理基础。由此可见,《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这二部小品集的出现,是时代、社会、思想、感情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它是晚明小品创作的最后辉煌。
纵观张岱的小品创作,有三个方面的主要内容。
第一方面的主要内容是表现张岱自己,实际上就是从多种角度表现了他那艺术化的生活态度。由于有实际的生活感受因而是小品创作中最为亲切的部分。
尽管张岱才华出众,但是他无意于仕途。(张岱并非无意于仕途,只是个人秉性与八股桎梏人性的规矩格格不入。)由于他家的经济条件优越,其生活无疑是奢侈浮华的,然而也培养了他多方面的生活情趣。他精于饮食,懂得“水辨渑淄,鹈分苍白,食鸡而知其栖恒半露,啖肉而识其炊有劳薪”。(く老饕集序》)他还精于茶道,对各种茶品的特性了如指掌。连当时著名的品茶专家闵文水也惊叹“余年七十,精饮事五十余年,未尝见客之赏鉴若此之精也”。(く茶史序》)。他上山能打猎,曾在牛首山带领百余人“极驰骤纵送之乐”,并且获得“鹿一、麂三、兔四、雉三、猫狸七”的战果。(《陶庵梦忆・牛首山打猎》)他平地会斗鸡,因为他鸡得法,他曾骄做地说,在斗鸡中,“余鸡屡胜之”(《陶庵梦忆・斗鸡社》)。了解到这些,就不难理解张岱的小品描写的生活为什么那样丰富多彩、具体生动。
当然,张岱过着这样的生活,与一般的公子哥儿有不同之处。他不仅能享受这样生活,而且还懂得如何创造这样生活。比如饮茶,他决不仅仅是像有闲人那样只知品鉴,他还懂得如何制作上等茶叶的劳动过程:“盖做茶之法,俟风日清美,茶须旋采,抽筋摘叶,急不待时;武火杀青,文火妙熟。”(《与胡季望》)他还认识到物质生活对人类的意义。比如饮食,他对“宋末道学盛行,不欲从口腹累性命,此道(指饮食)置之不讲”深表不满,认为着衣食饭”,“要之帝王家法亦不能外”(老饕集序》)。而且,张岱一旦认识到他所追求的某种生活并无益处,还有自我克制的意志和毅力:“一日余阅稗史,有言唐玄宗以西年酉月生,好斗鸡而亡其国。余亦西年西月生,遂止。”其实,斗鸡与亡国并无必然联系,只是从这里可以看出张岱决不像公子哥儿沉湎于浮华生活而醉生梦死,不能自拔。因此,过去不少文学史与论著笼统地说张岱在明亡之前过着公子哥儿生活,并不十分恰切。
还应该看到,张岱的浮华生活,有的是他对艺术生活的挚热追求。他有很高的音乐修养。他是位出色的演奏家,曾向王侣鹈请教,学习了《渔樵问答)、《列子御风〉、《碧玉调》、《水龙吟〉、(捣衣环佩声》等曲子,又曾向王本吾请教,半年学习了二十多个曲目:《雁落平沙》、《山居吟》、《静观吟》、く清夜坐钟〉、《乌夜啼)、汉宫秋〉、(高山流水〉、《梅花弄〉、《淳化引〉、《沧江夜雨〉《庄周梦》,还有《胡笳十八拍〉、く普庵咒》等小曲十余种。他为了提高演奏技艺,成立过丝社,“月必三会之”,要“共怜同调之友声,用振丝坛之盛举”。(《陶庵梦忆・丝社》)而且,张岱通过学琴领悟到艺术辩证法的重要性:“弹琴者,初学入手,患不能熟;及至熟,患不能生。夫生,非涩勒离歧、遗忘断续之谓也。古人弹琴,吟揉掉注,得手应心。其间勾留之巧,穿度之奇,呼应之灵,顿挫之妙,真有非指非弦、非勾非别,一种生鲜之气,人不及知,己不 及觉者。非十分纯熟,十分淘洗,十分脱化,必不能到此地步。”这是演奏的最高境界,已达到炉火纯青的地步。张岱还认识到这种艺术辩证法通于其他文艺:“盖此练熟还生之法,自弹琴拔阮,蹴吹簫,唱曲演戏,描画写字,作文做诗,凡百诸项,皆藉此一ロ生气。得此生气者,自致清虚;失此生气者,终成渣秽。”(《(与何紫翔》)难怪张岱的小品创作如行云流水那样清新自然看来并不是偶然的。
张岱也是醉心于戏曲的行家。祖父在家先后办起了那么多戏班,使他从小就受到了耳濡目染的影响。因而,他能创作戏曲,“魏珰败,好事作传奇十数本,多失实,余为删改之,仍名《冰山)”。演出后戏剧效果极佳:“一人上白曰:'某杨涟。'口谇谅日:杨涟!杨涟!'声达外,如潮涌,人人皆如之。杖范元白,通死裕妃,怒气忿涌,噤断喈。至颜佩韦击杀缇骑,呼跳蹴,汹汹崩屋。沈青霞缚藁人射相嵩以为笑乐,不是过也。”有人对他创作戏曲提出意见,他也能认真听取,连夜修改(《庵梦忆・冰山记》)。他还善于导演戏曲,有一个演员叫杨立,由于张岱指导得法,演出才较为成功,所以,这个演员“嗣后曲中戏,必以余为导师,余不至,虽夜分不开台也。”(《陶庵梦忆・过剑门))从中他体会到戏曲创作和演出之所以成功的关键所在。他称赞阮大铖的戏班,就在于他们“讲关目,讲情理,讲筋节,与他家孟浪不同”,而且注意戏曲底本的质量:“然其所打院本,又皆主人自制,笔笔勾勒,苦心尽出,与他班卤莽者不同。”同时还要求演员懂得剧作的义旨:“余在其家看く十错认》、《摩尼珠〉、《燕子笺》三剧,其串架斗笋、插科打译、意色眼目,主人细细与之讲明。知其指归,故咬嚼吞吐.、寻味不尽。”因而在演出中,无论是道具、无论是人物,都能传神:“至于《十错认》之龙灯、之紫姑,《摩尼珠)之走解、之猴戏,《燕子笺》之飞燕、之舞象、之波斯进宝,纸札装東,无 不尽情刻画,故其出色也愈甚。”(《陶庵梦忆・阮园海戏》)但他又注意反对戏曲中“只求闹热,不论根由,但要出奇”的错误倾向要求戏曲讲究“文理”。他在く答袁箨庵》中说:“只看《琵琶〉、《西厢),有何怪异?布帛菽粟之中,自有许多滋味,咀嚼不尽。传之永远,愈久愈新,愈淡愈远。”张岱这种文艺思想不能不影响他小品创作。他的小品之所以既平易又传神,这种文艺思想无疑是内在因素。
另外,张岱对绘画、书法艺术也有较高的造诣。比如,他为精于制印的胡兰渚作序时,曾自信地说过:“余酷好印章,亦曾深加考究。咄咄兰渚,幸勿以门外汉目之。"(《印汇书品序》)…很明显,张岱在广泛的艺术活动中,结交了许多著名的艺人。张岱尊重这些人的人格,赞赏这些人的技艺。在他的朋友中,有工艺美术家仲谦,“雕刻妙天下,其所制别帚尘柄,筋瓶笔斗,非树根盘结,则竹节支离,略旋斧斤,遂成奇器,所享价几儿与金银争重”。“彼仲谦一假手之劳,其所制器,置之商彝、周鼎宣铜、汉玉间,而毫无愧色”。(《陶庵梦忆・沿仲谦雕刻》)有画家陈章侯,张岱因他创作《水浒》中四十个英雄画像而深情地赞叹“余友章侯,才足掞天,笔能泣鬼,昌谷道上,婢囊呕血之诗,兰渚寺中,僧秘开花之字。兼之力开画苑,遂能目无古人。”"(《陶庵梦忆・水浒牌》)还有演员朱楚生、彭天锡,张岱对朱楚生认真作戏由衷敬佩:她“性命于戏,下全力为之,曲白有误,稍为订正之,虽后数月,其误处必改削如所语”。(《陶庵梦忆・朱楚生》)张岱对彭天锡出神入化的表演更是赞不绝口:他“到余家串戏五六十场而穷其技不尽。天锡多扮丑净,千古之奸雄佞幸,经天锡之心肝而愈很,借天锡之面目而愈刁,出天锡之口角而愈险,设身处地,恐纣之恶不如是之甚也、皱眉舐眼,实实腹中有剑,笑里有刀,鬼气杀机,阴森可畏。盖天锡一肚皮书史,一肚皮山川,一肚皮机 械,一肚皮碟砢不平之气,无地发泄,特于是发泄之耳”。(《陶庵梦忆・彭天锡串戏))正因为张岱对这些艺人有着真诚的感情,所以许多艺人乐与他相交。像姚简叔这样的画家,本来是“落落难合,孤意一往”的人,但与张岱,却“不知何缘,反而求之不得也”。(《陶庵梦忆・姚简叔画》)
毫无疑义,张岱也性好山水,喜欢漫游。他在く大石佛院》诗中写道:“余少爱婷游,名山恣探讨。”他对杭州西湖一带的风景极为熟悉,可以说无处不到,而且,每到一处都细细观察、鉴赏。当然,他还北上到过泰山,看过孔林,谒见过孔庙桧,这些都给他留下极深的印象。那南京的燕子矶、钟山,不用说也要留下张岱的足迹。镇江的名胜古迹,他更是探寻过多次。他说:“仲叔守瓜州,余借住于园,无事辄登金山寺。风月清爽,二鼓,犹上妙高台,长江之险,遂同沟浍。一日,放舟焦山,山更行谲可喜。江曲过山下,水望澄明,渊无潜甲。海猪、海马,投饭起食,驯扰若豢鱼。看水晶殿,寻瘗鹤铭,山无人杂,静若太古。回首瓜州,烟火城中,真如隔世。”(《陶庵梦忆・焦山》)真是别有体会。至于苏州的虎邱、扬州的二十四桥,他那妙笔生花的小品创作,就是他曾流连忘返、恣意赏玩的见证。…总而言之,各处的山水风景也是促发张岱灵感的“酵母”。这部分的创作,是其小品中极其重要的一部分。
张岱小品创作的第二个方面的主要内容,是他多彩多姿地描绘了晚明的社会习俗和人情世相。他勾勒的生活场景,是如此生动,如此富有情趣。比如清明时节的扬州:
扬州清明,城中男女毕出,家家慕。虽家有数墓,日必展之,故轻车骏马,萧鼓画船,转招再三,不辞径复。监门小户,亦携般核纸钱,走至所,祭毕,席地饮胙。自钞关南门、古渡桥、天宁寺、平山堂一带,枧妆藻野,被服缛川。 随有货郎,路傍摆设骨董古玩并小儿器具。博徒持小机坐空地,左右铺袒移半臂、纱裙汗悦、铜炉锡注、瓶溱奁,及肩彘鲜鱼、秋梨福橘之属,呼朋引类,以钱地,或六或八或十,谓之六成入成十成焉,百十其处,人环视之。是日,四方流寓及商西贾、曲中名妓,一切好事之徒,无不成業。长塘丰草,走马放鹰;高阜平网,斗鸡蹴,茂林清树,劈阮弹笋。浪子相扑,童稚纸鸢,老僧因果,替者说书。立者林林,蹲者蛰蛰。
风俗往往是某地千百年来群众文化的积累和凝聚,反映着一个地域的特点,它那鲜明的地方色彩和特殊形态给人们会留下深刻印象,因而,成功的风俗描写是文学具有光彩的极其重要因素,张岱恰恰擅长于此。他在栩栩如生描绘过扬州清明后又说“余所见者惟西湖春,秦淮夏,虎邱秋,差足比拟。”如果一一迫寻张岱笔下这些生活场景,就会惊叹张岱这方面的才能。现在再看看他笔下的端午节时的秦淮河:
年年端午,京城士女填滋,竟看灯船。好事者集小船百什艇,上桂羊角灯如联珠。船如触龙火,屈曲连姥幡委旋折,水火激射。舟中馓钱星饶,宴歌孩管,腾腾如渧。士女凭栏轰笑,声光凌乱,耳目不能自主。午夜,曲倦灯残,星星自散。
这种繁华的景象,反映着晚明社会生活的奢靡。至于《虎邱中秋夜》、《西湖七月半》,这些脍炙人口的名篇,对世俗生活的描绘更是人们熟知的。
(张岱和宝玉一样,都是能在繁华中窥视到落寞的特殊的那一个人。极其善于思考。)
当然,包含着多方面的沉淀的历史内容的社会风俗,有的也反映着封建统治阶级的恶习。对于这些,张岱也曾加以细致的描绘,比如《扬州瘦马》就是较为生动的一篇:
至疲马家,坐定,进茶,牙婆扶瘦马出日:“姑娘犴客。” 下拜。曰:“姑娘往上走。”走。日:“姑娘转身。”转身向明立,面出。曰:“姑娘借手閘。”尽褫其袂,手出,臂出,肤亦出。日:“姑娘閘相公。”转眼倫觑,眼出。日:“姑娘几岁了?”曰:九岁,声出。日:“姑娘再走走。”以手拉其裙,趾出。然看趾有法,凡出门裙幅先响者必大,高条其裙,人未出而趾先出者必小。曰:“姑娘请回。”一人进,一人又出。
所谓“瘦马”,原来是富人为了纳妾在市场上挑选的妇女的代称,她们已丧失了人格,变成了一件货物。这正是封建社会广大妇女的悲惨命运的真实写照。至于妓女接客的情景,更是浸透着血泪:“剩者不过二三十人。沉沉二漏,灯烛将烬,茶馆黑魃无人声。茶博士不好请出,惟作阿欠,而诸妓醵钱向茶博士买烛寸许,以待迟客。或发娇声唱く劈破玉〉等小词,或目相谑浪嘻笑,故作热闹以乱时候,然笑言哑哑声中,渐带凄楚。夜分不得不去,悄然暗摸如思,见老鸨,受儼、受答,俱不可知矣。”看来,这些描绘不仅具有艺术价值,而且,对民俗学来说,具有史料价值,是研究纳妾史与娼妓史的材料。
张岱不但善于描绘晚明社会的世俗生活,而且善于勾勒和表现活跃在晚明社会环境里的各色各样的人物。这是张岱小品创作的第三方面的主要内容。很显然,小品“塑造”人物并不像小说那样,通过情节的运动来展现人物的性格,而是抓住一个或几个典型事件,传神地突出地描画人物,而且,在描画人物时,往往倾注着作者本人的感情和评价。比如张岱表现艺人柳敬亭他只是突出他说书时的创造性以及出神入化之处:
余听其说“景阳岗武松打虎”白文,与本传大异。其描写刻画,微入毫发,然又找截乾净,并不唠叨。夫声如巨钟。说至觞节处,叱咤叫喊,沟沟崩屋。武松到店沽酒,店内无人,琴地一吼,店中空缸空党皆翁翁有声。间中著色, 细微至此。
正因为如此,张岱对他进行了由衷的赞美:“柳麻子貌奇丑,然其口角波悄,眼目流利,衣服恬静,直与王月生同其婉娈,故其行情正等。”又如,张岱刻画他的友人王思任,就突出了他“出言灵巧,与人谐谑”的特征。当然,这种诸谑,决不是给人解解闷儿,而是表现了王思任强项的性格和过人的机智。他曾以诸谑而解“两都之厄”:
中书程守训奏请开矿,与大珰邢隆同出京,意欲开采从当涂起,难先生。守训運留瓜州,而赚珰先至,且勒地方官行属吏礼,一邑骚动。先生曰:“无患。”驰至池黄,以绯袍投刺称生。瑾怒诃,谓县官不亲服。先生曰:“非也。俗礼吊则服素,公此来庆也,故不服素而服绯。”珰意稍解。复话曰:“令刺称着何也?”先生曰:“我固安阳状元也,与公有瓜葛。”珰大笑,亦起更绯,先生坐上座,设饮极欢。因言及横山,先生日:“横山为高皇帝吊湖龙首,樵苏且不敢敢问开采乎?必须题请下部议方可。”当日:“如此利害,我竟入矣。”先生耳语曰:“公无轻言入徹也。後人大无状思甘心于公左右者甚众。我为公多奋劲卒,以护公行。”珰大惊日:“吾原不肯来,皆守训赚我,”先生日:“人恨守训切骨,思磔其肉,而以骨何狗。渠是以观望爪州,而赚公先入虎穴也。”珰曰:“公言是,我即回京,以公言复命矣。”当涂、徼州得以安堵如故,皆先生一之力也。
或许这些描写有某些艺术夸张之处,但却传神地表现了王思任的风貌。这又是张岱小品创作的过人的地方。
当然,张岱的小品创作在中国文学发展历史上的意义,还在于在艺术上也取得了不少开拓性的成就。首先是表现在语言上。必须指出,语言的选择和方式的变化,决不単纯是一种艺术 表现手法的创新,它实际上反映着作家的思维方式和文化心态的变化。阅读张岱小品,印象最深的莫过于俚俗化了,这与唐宋八大家也有显著区别。上面所举的张岱描写富人挑选扬州瘦马一一妇女为妾的那段,语言就似口语一般。我们再看看《夜航船)中一段描写:
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儅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是两个人?”士子日:“是两个人。”僧日:“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日:“自然是一个人。”僧人ろ笑日:“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余所记載皆眼前极肤极浅之事,吾辈聊且记取、但勿使僧人伸脚则亦巴矣,故即命其名曰夜航船。
张岱之所以选择这样俚俗的语言,正是因为他认识到,要表现社会的习俗和人情世态,要表现“极肤极浅之事”,这样的语言表达方式是最逼真的描绘,能产生身临其境的强烈效果。这不仅是语言革新,而且是艺术创新。
不用说,张岱的小品语言清新自然,但这并不出奇。真正令人惊叹的是,他能巧妙地配置语言,使语句与语句之间产生必要的张力,造成一种绘画美,自然创造出一种意境。比如《湖心亭看雪》:
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是日更定矣,余孥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雾松沆砀,天与云、与山、与水,上下一白,湖上彩子,惟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与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而巴。到亭上,有两人铺毡对坐一童子烧酒炉正沸。见余大喜日:“湖中馬得更有此人!”拉余同饮。余强饮三大杯而别。问其姓氏,是全陵人,容此。及下船,舟子喃喃曰:“莫说相公,更有病似相公者。
这里运用的语言都很普通,但配置得极其绝妙:“大雪三日,湖中人鸟声俱绝”与紧接而来的“余一小舟,拥毳衣炉火,独往湖心亭看雪”形成强烈的反差,使“余”的独特个性传神地烘染出来而“长堤一痕”、“湖心亭一点”、“余舟一芥”、“舟中人两三粒”这样连续的排列,就自然展现出一幅绘画长卷,而且线条如此清晰。语言在张岱笔下真有巨大的魔力!其实,在这种语言创造里,包含着艰辛的艺术探索。至于说,用一痕形容长堤、用一点形容湖心亭、用一芥形容小舟、用两三粒形容舟中人,其用词的准确、生动,那更是容易体会的了。
(张岱的炼字技巧登峰造极,红楼梦程本的遣词造句十分精当。而脂本水平低劣,不可不察。)
说起张岱小品的创作风格,他的朋友发表过不少较好的议论,比如王雨谦在《西湖梦寻序》说他“记如袁石公之灵巧,张钟山之道劲,李长蘅之淡远”,祁易佳的序也认为他“笔具化工,其所记游,有郦道元之博奥,有刘侗之生辣,有袁中郎之情丽,有王季重之诙诸,无所不有。其一种空灵晶映之气,寻其笔墨又一无所有”。这些议论给人们一个很好的启示,说明张岱小品的表现手法的多样化,所谓“灵巧”、“淡远”也好,所谓“生辣”、“诙谐”也好,在其创作中都有表现。然而,这些并不是杂乱无章凑合在起,而是吸取各家之长,自成独特的风格。其追求的最高境界则是能生动逼真描绘世俗人情,这一点张岱是基本上达到了,因而艺术上能给人以整体美。这是文艺创作的最高奖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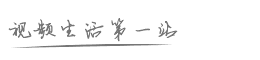






 quyi56
quyi56